
國家二級心理咨詢師 關 注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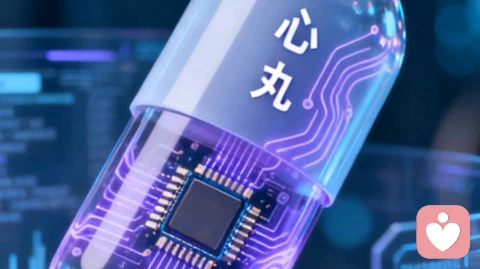
當來訪者自我動搖時,「定心丸」有哪些給法,為什么?
當來訪者自我動搖時,「定心丸」有哪些給法,為什么?
從東西方文化差異與心理學流派說起作為一名從業多年、累積超過4700小時咨詢時數的整合取向咨詢師,我常常遇到這樣一個問題:當來訪者陷入自我懷疑、內心動搖的時刻,我們該如何給予他們真正的支持?是直接給出一個堅定的答案?還是一起慢慢探索?又或是長久陪伴、靜待花開? 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,對于隸屬于某一理論框架/流派/文化體系的心理咨詢師其實還挺容易自主的,只要認同這個框架,按照要求去做就好了,而對于我這種,從西方心理學培訓體系里萌芽,在文化差異間奔襲,最終想整合一些,多元一些的整合取向咨詢師可能都要經歷一個過程,在這個過程中淬煉自己的風格。
這是一個極具爭議的話題,對于隸屬于某一理論框架/流派/文化體系的心理咨詢師其實還挺容易自主的,只要認同這個框架,按照要求去做就好了,而對于我這種,從西方心理學培訓體系里萌芽,在文化差異間奔襲,最終想整合一些,多元一些的整合取向咨詢師可能都要經歷一個過程,在這個過程中淬煉自己的風格。
事實上,這不僅僅是一個技術問題,更是一個文化立場、哲學觀念與治療理念交織的深刻議題。今天,我們就來聊聊三種常見的“給法”,以及它們背后的文化邏輯與人性假設。
?? 一、直接點撥:來自“貴人”的智慧
文化背景:東方傳統中的權威與啟示這種方式非常“中國”。我們從小就聽過“高人指點”“貴人點撥“長輩一句話點醒夢中人”的敘事。
它背后是一整套文化體系:
· 儒家的尊卑秩序與師道尊嚴
· 道家的“明心見性”“頓悟”傳統· 家族系統的集體主義價值觀——智慧常被認為蘊藏在長輩、師傅或經驗之中
在這樣的語境中,咨詢師某種程度上扮演了一個“智者”或“引導者”的角色,給予明確的方向性建議。
為何西方較少這樣“給”?
西方更強調個人主義與自我決斷,心理學傳統也更警惕權威依賴。宗教中雖然也有“神父指導”,但現代心理治療更傾向于把人看作“自己問題的專家”以及“線性因果論”。
?? 二、共同建構:兩個人一起創造的定心丸
貼近:主體間性與拉康式的“同行”這是我最偏愛也最常用的方式之一。它不來自某一方的“給予”,而是兩人共同建構的理解與確認。
拉康所說的“無意識是大他者的話語”,其實也暗示了:意義是在關系中浮現的。
主體間的關系本身更是來源于量子糾纏的啟示:任何階段,任何關系都存在無限的可能與超越。
這種方式:
· 不否定主體的能動性,也不拋棄引導的責任· 強調此時此地的互動與真實相遇
· 融合了人本主義的共情、存在主義的選擇與后現代的建構意識它適合那些既渴望被理解,又不愿失去自主性的現代人——尤其是青年群體與LGBTQ+人群。
? 三、長期陪伴:打破、重來與緩慢生長
心理動力學:看見真實的自己,需要時間這是經典動力學派的做法——不急于“給答案”,而是陪伴來訪者經歷情緒與記憶的重整。通過詮釋、自由聯想、夢的分析等方式,逐步解開防御、觸碰真實。
科胡特說:“共情本身就是一種治療。”
比昂說:“沒有記憶與欲望,只是存在。”
這種方式拒絕快餐式的安慰和“簡單粗暴”的點撥,相信:真正的定心丸,不是別人給的,而是自己長出來的。
那么,哪種方式更好?
誰來決定?
沒有絕對答案。
我個人的工作理念是:
不以流派為框,而以人為鏡。
不定標準答案,但求匹配真實。
有些來訪者需要一句堅定的話——比如某些孕產期女性在焦慮中需要一個科學的解釋;有些人需要被深沉地理解——比如青少年在身份認同中的迷茫;也有些人,需要在長程關系中慢慢修復早期創傷——比如某些人格層次的困難。 誰說了算?
誰說了算?
不是理論,不是文化,也不是咨詢師——是咨詢師與來訪者共同工作的那個“之間”(the between)。
定心丸,本質是一種相遇
我始終相信,最好的“定心丸”,不是一句話、一個技術,而是一段真實、可信、包容的關系。它可能源于一句適時的話,可能來自一段共同的理解,也可能來自長期的陪伴與見證。
而作為咨詢師,我所做的——是保持理性的共情,沉穩的探索,以及,永遠對“人”的深度好奇與敬畏。
? 文/ 理性的共情者(整合取向心理咨詢師 | 深耕臨床10年 | 陪你看見真實,也看見可能,看見不執著)
 李洪文
516 0
李洪文
516 0



